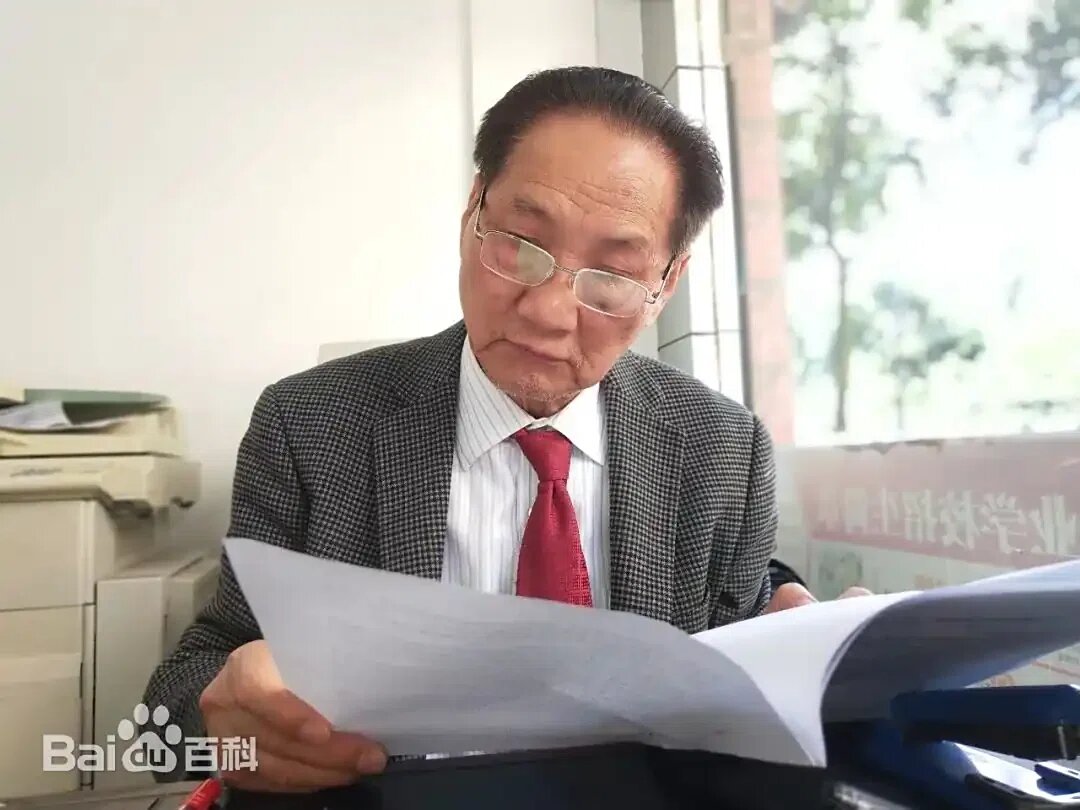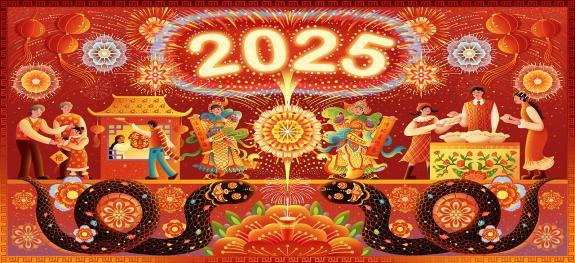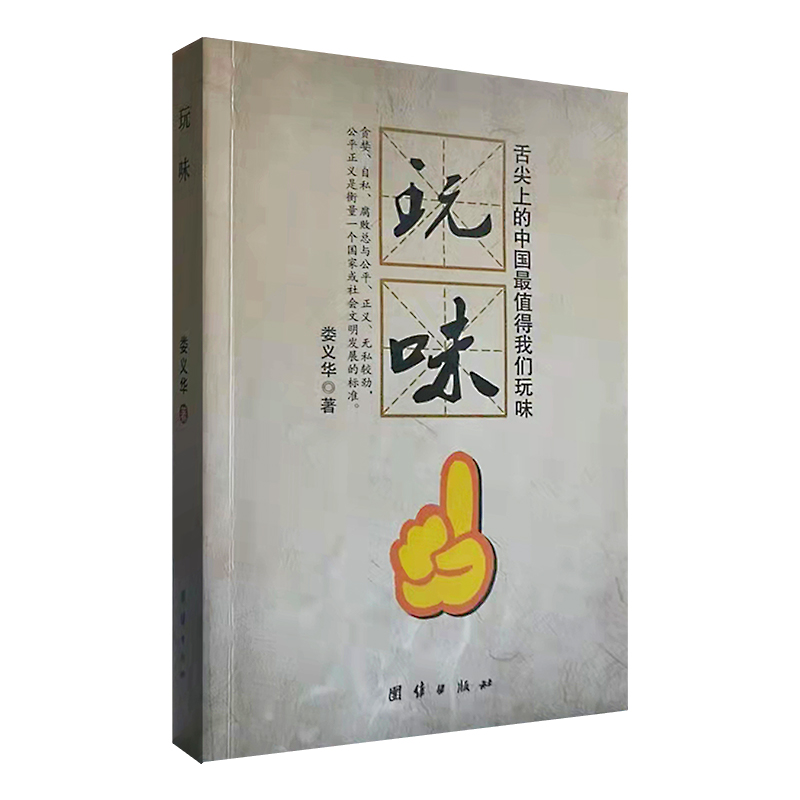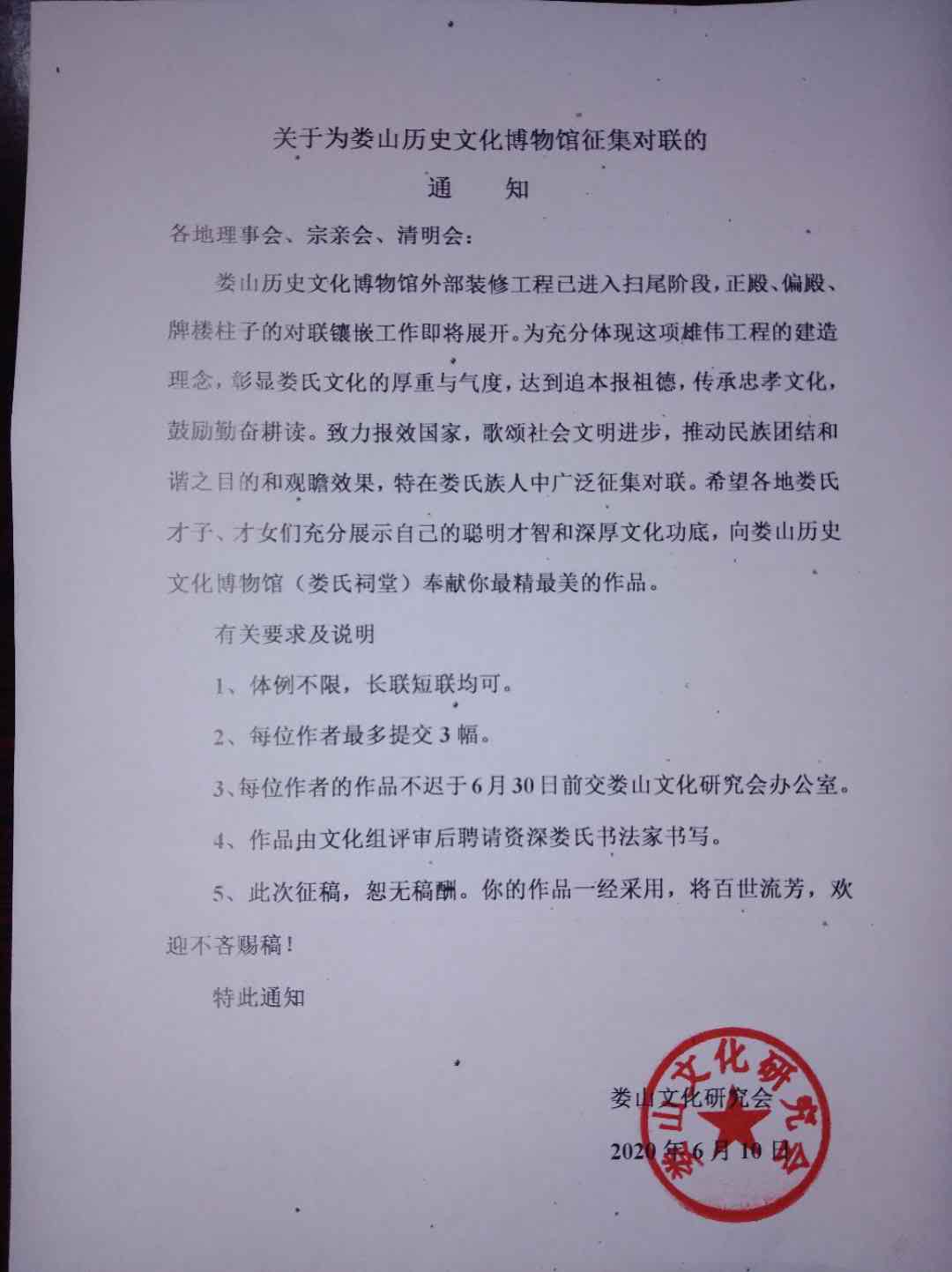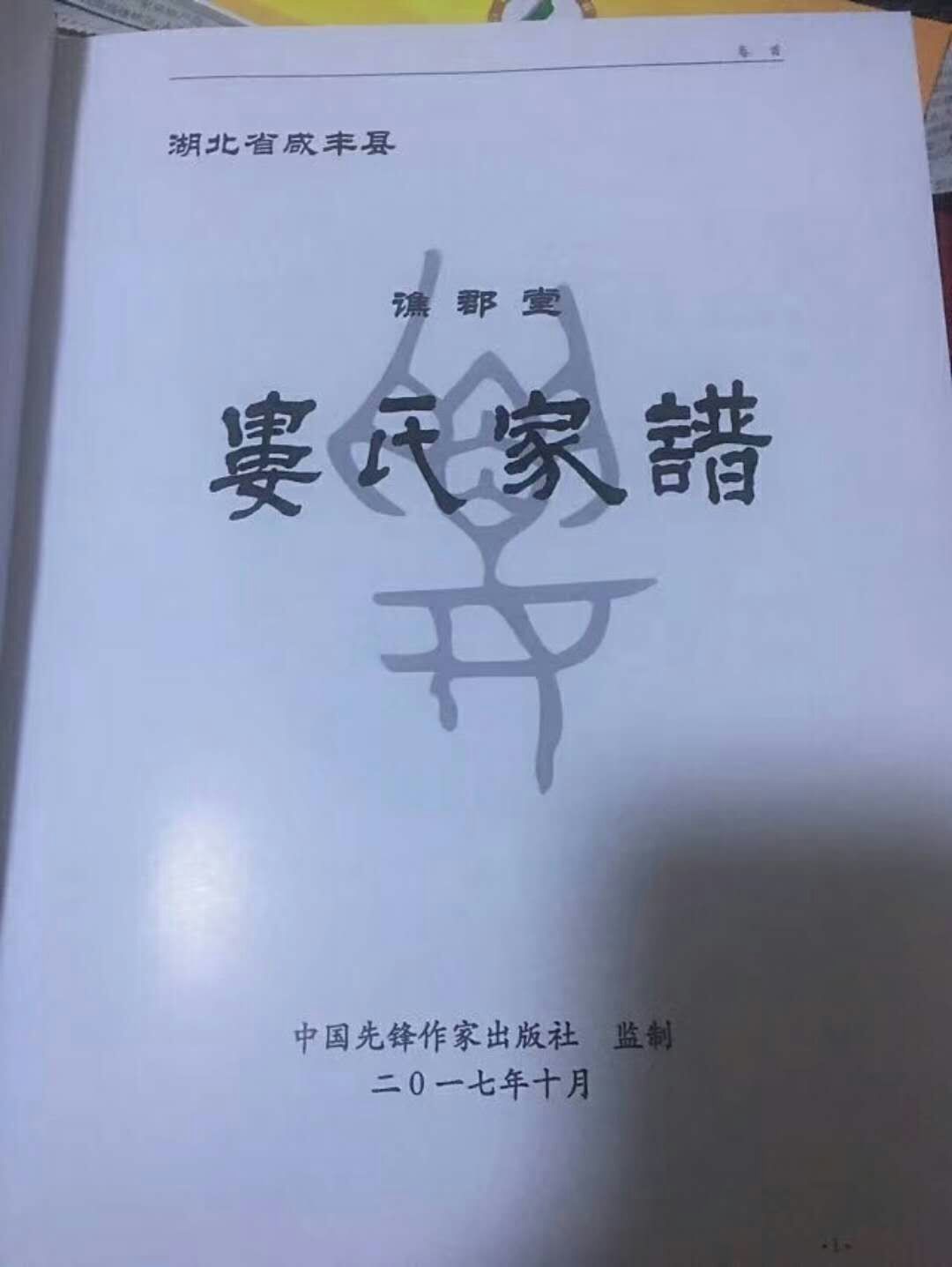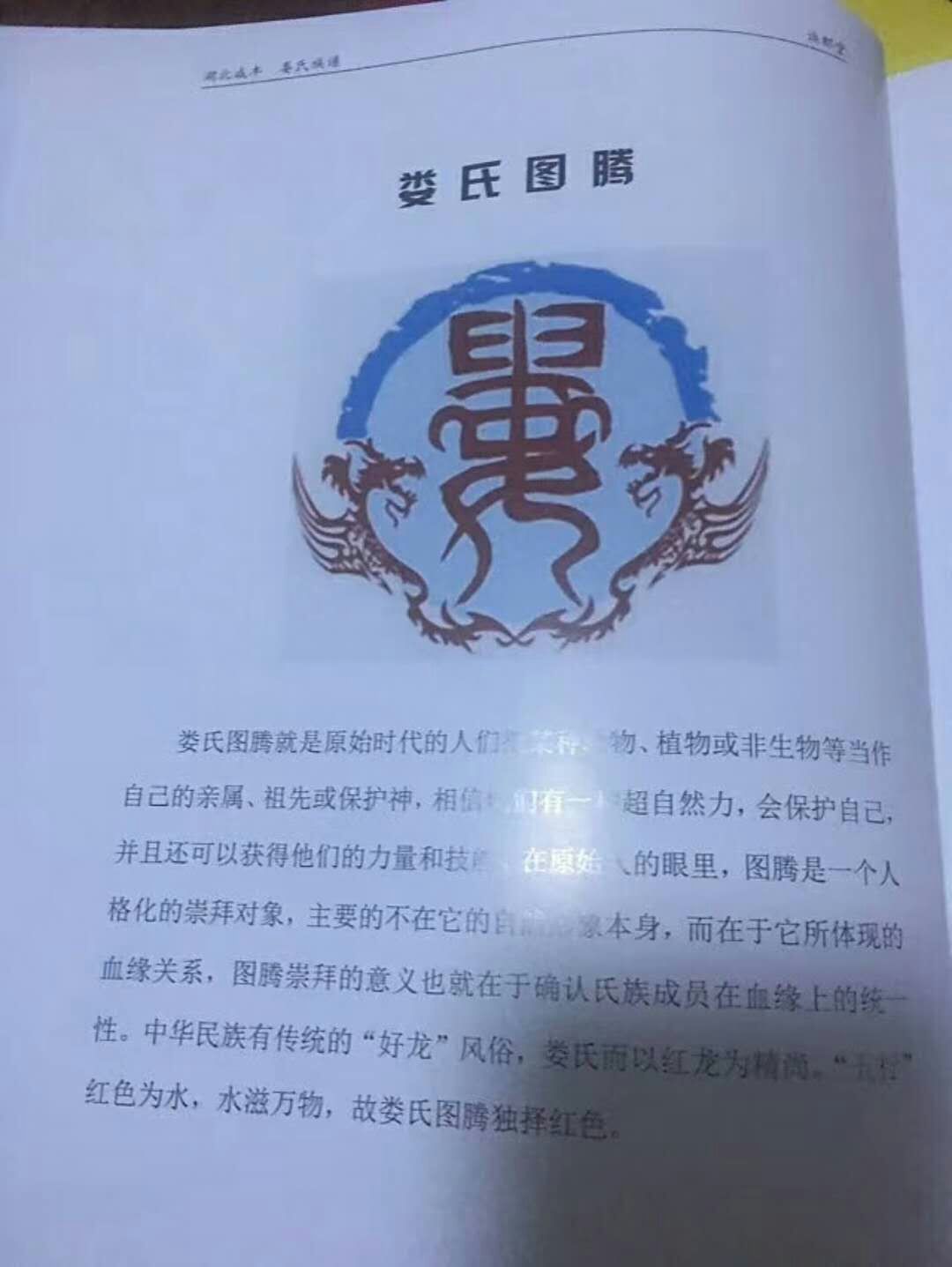梁正乾:黔北地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关于黔北地区历史的整理和发掘,许多专家学者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学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的浓厚兴趣。本人没有对地方历史进行过研究,无法对一些历史存疑做出正确的判断,偶尔阅读地方史籍,思想里产生了一些疑问,就是:黔北地区的民族人口、经济文化迥异于贵州其它地区,这是如何形成的?这里在云贵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者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因此,本人自求其解地认为,今天黔北地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人口结构和文化特征,与历史上有计划的大规模移民黔北有直接关系,人口的自然迁徙产生次要作用;这一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是中央政府在云贵地区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的前方大本营,是历代朝廷控制云贵高原的一个“桥头堡”,在云贵历史发展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些想法,仅仅是个人偶尔读史的一点体会,未作专门研究,今将想法提出,不讳齿冷,以供学界参考。

娄山关历史文化研究会现场。
一、移民的社会
众观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人口迁徙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众多姓氏中大部分都是起源于北方,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向南发展,有的姓氏甚至在北方已经少有,而在南方却是人口众多。出现这一历史现象,是官治移民和自然迁徙共同作用的结果,官治移民也就是朝廷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派遣军队(军事世家)或文职官员到南方治守,其中不少被令定居南方。遵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治移民社会,这里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代受命治守黔北地区将领和治官的后裔。
黔北地区的民族、社会、文化与其它地区有很大差异。这里的人口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其社会管理、文化发展都融入了更多的中原历史文化元素。在其邻近的毕节、铜仁、黔南乃至贵阳等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和文化所占比重都很高,只有黔北地区与云贵高原各地迥然不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口和文化体系。历史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汉民族来到黔北地区定居,这其实就是移民,准确地说就是官治移民。过去有些人讲,黔北地区受四川文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在贵州与众不同。我觉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恰恰忽视了该地区在民族、人口方面与周边地区的巨大差异,正是民族、人口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差异。
今天的黔北地区人口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迁入,他们或来自江西、或来自湖广、或来自四川,各自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定居于此,这里有很多姓氏都明确记载了自己的迁入历史,其中不少记载何时何事受命到黔北地区征战并定居,他们其实就是官治移民,比如:罗、穆、何、杨、令狐、成、犹、娄、梁、谢、袁等姓,都是在一定时期受命治守并定居黔北地区的姓氏,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末“随杨入播”的历史事件,也就是八大姓军队随主将杨端征战并定居黔北。胡大宇先生《关于桐梓县境土司与土官研究》一文强调:历史上桐梓境内的土司土官“均为外地奉旨迁入,以战功受朝廷封赏,奉朝廷为正统,以朝廷的名义统治辖地”。因此,遵义的社会文化更多地是随人口的迁入而植入,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直接移入,再融入了当地文化和周边文化(包括川渝文化),从而形成了遵义的地域特色文化。
二、曾经发生的琐碎故事
黔北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结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朝历代都把这里作为进入云贵高原的“桥头堡”,把它当作控制云贵高原的前沿阵地。西南地区远离华夏中心地带,古代交通闭塞,民族、文化、风俗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要实现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必须建立一个前沿阵地。纵观历史发展,遵义就是历代王朝控制云贵高原的一个典型的有保障的前进基地。早在秦汉时期,遵义就已列入华夏版图。汉朝建立后,为了控制南越国,汉庭对云贵高原上的夜郎国采取了安抚政策,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出使夜郎,从四川进入黔北地区。唐蒙见到了夜郎王多同并取得了他信任,还报朝廷后,汉庭在今遵义境内设置了健为郡。至今,在桐梓境内还留有“蒙渡”、“蒙山”等唐蒙出使夜郎国留下的地名遗迹。
黔北地区开始置郡后,就成了历代朝廷征战和治理西南边陲的前沿阵地,成了云贵高原军事政治的“大本营”。一方面历代多有军队在这里“扎根”,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支援西南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一做法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高潮。唐朝中后期,南诏国崛起,与大唐对峙并经常发生摩擦,朝廷多次派遣军队占领并统治黔北地区,先后有罗荣、穆天星、杨端等所属军队屯居于此。经历了平定南诏国侵扰的战争后,杨端及其所率的娄殿邦、梁宗理等姓军队定居并世袭统治黔北地区,中原王朝在云贵高原上真正“站稳了脚跟”,从此未被西南小国侵扰。此后的宋朝、元朝、明朝建立后,都肯定并沿袭了黔北地区这种“军屯”的治理模式。期间,仍有一些军人继续被派遣到这一地区定居,比如宋代入籍习水定居的袁姓将领及其部属;居住在桐梓的令狐姓,在唐末平定南诏之战后定居于阆中,明初再次征战黔北并受命定居于此。
古代在黔北地区的这些军事政治活动,也留下了不少历史遗迹,比如:“穆家川”是穆氏受命定居时最早居住的地方;“娄山关”是因娄梁二姓军队长期镇守而被称为“娄珊梁关”,后来逐渐演变成“娄山关”。桐梓楚米这一地名更是体现了黔北地区作为前沿军事基地的地位和作用。明清时期,西南战事频繁,朝廷为了保障前方作战需求,从四川、湖北等地运送稻谷到楚米囤积,根据前方战事需要及时输送到前线。那时在这里出现了很多加工作坊,将稻谷加工成大米,因此便被称作“杵米铺”,后来演变成了楚米铺、楚米。解放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地带的黔北地区,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军事保障基地。
三、缘由起底
为什么黔北地区在古代会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云贵高原的前沿阵地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具有特殊的区位。黔北地区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紧邻四川盆地,是四川盆地进入云贵的必经之路。从四川盆地进入云贵高原,首先要在黔北地区站稳脚跟,军事和政治力量才有条件向黔中及云南地区推进。只要占据了黔北地区,就突破了川黔交汇地带的一道道地理屏障,南进贵阳、西取毕节就变得十分容易。
二是具有充裕的后方保障。黔北地区邻近的四川盆地是富庶之乡、天府之国,那里开发较早,人口多、生产发达,粮草物资充裕,是支援云贵前线的一个大后方。再者,连接华中地区的黄金通道长江,能够将大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粮草物资、军队运到重庆一带,及时送往前线。以黔北地区为控制云贵的前进基地,其后方保障十分有力。
三是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在云贵高原隆起的川黔一带,地势切割强烈,山高谷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在南面是乌江天险,是屯兵守战的理想环境,进可攻、退可守,既有利于凭借关隘固守后方,又有利于迅速出兵前线,有效支援前方发生的战事。
四是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遵义府志》云:“唐蒙谕夜郎侯多同,约置吏,使子孙为令,西南始郡县焉”。说明黔北地区开发相对较早,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云贵其他地区好,成为南通北达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川黔交往的重要走廊,人口物资流动频繁,在社会文化方面较为充分地融入了中原地区元素,有利于军队的屯驻和发展。
可以说,黔北地区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古代支援云贵战事的必经之地,因此受到了历代的重视和充分利用。毗邻川颠的黔西北和毗邻湖广的黔东地区都不具备这些优势。黔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相对基础较弱,川渝及中原文化融入较晚,且距离西南夷国部落地区较近,虽有一些天然屏障,但仍容易受到攻击;黔东地区地理自然理条件虽然较好,但其后方保障基地不够坚实,且纵深较大、路途遥远,战争支援难以及时保障。
四、社会文化特征
黔北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也与贵州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别。
首先,在居住上,黔北地区农村居民以散居为主,以村寨形式集中居住的比较少,以村落为单元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文化也不明显,远近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没有多大的差别,相互之间认同感普遍较强。而在周边的其他地区,民众则以聚集居住的形成村寨,村寨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其内部认同感较强,村寨之间、地区之间认同感则稍逊。
其次,在语言上,黔北地区使用汉语的民众占绝大多数,在使用汉语的人群中,各地的语言差别也比较小。这不但是各地间生产生活交流比较充分形成的,也与当地居民迁入源头的一致性不无关系。黔北地区居民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民俗节日,这也表明他们不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族群,而是中原南迁人口中的一部分。
第三,在古代的婚嫁、丧葬习俗方面,黔北地区与贵州各地也有不小的区别,反而与川渝地区及中原地区比较接近。比如,贵州古代不少地区青年有对歌成嫁的习俗、有母舅主婚的习俗,而在黔北地区,古代主要是父母包办婚姻,与中原、川渝地区基本相同。
第四,在社会管理方面,贵州很多地区以往往以村落或民族为单元,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比较牢固的自我管理体系,他们多以部族中的长者为尊,并有自己的一套部族规矩和部族文化。而在黔北地区,这样的自我管理体系十分少有,虽然过去一些姓氏中有族长管理体系,但也是在清朝早期根据朝廷圣谕要求建立的,与官府的管理“相辅而行”,严格地说只是官方管理的补充和延伸。
以上这些都这表明,黔北地区的居民在民俗、语言、生产等方面存在着相对一致、与周边地区有较大差异的特征,这体现了当地民众的来源相对比较统一。
五、其它
黔北地区存在众多军事世家的后裔,曾经被一些人质疑,他们认为不可能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军事将领的后代。这种认识,显然是对这里的特殊历史发展不了解所造成的,他们用通常的眼光去看待具体问题,对一个地方的历史不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用一般规律去解读特殊个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黔北地区在其所在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突破单一研究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苑囿,更好地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南北各地的人口族群中,大多数家族都声称自己是官宦家族的后裔,黔北地区的各族姓则更为突出。形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少族姓(家族)或早或迟都有一两个先辈或更多的先辈曾经做过官,这些族姓通常都以最显赫的祖先后裔自居,这并不是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显赫之家,而是在众多祖先中曾经有人做过官。二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社会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官宦之家往往妻妾成群,因此他们繁衍的后代多,如此发展,一代接一代其子孙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经历了数千年之后,官宦家族的后裔自然占有极大的比重。所以,很多的族姓说自己是将门之后或官宦之后,这就不足为奇,这是历史发展优胜劣汰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人口发展的真实状况。
(作者简介:梁正乾,遵义市桐梓县老龄委主任、壁上挂灯梁氏研究会副会长)
(娄山关历史文化研讨会征集作品)
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
【编辑:陈华】
阅读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