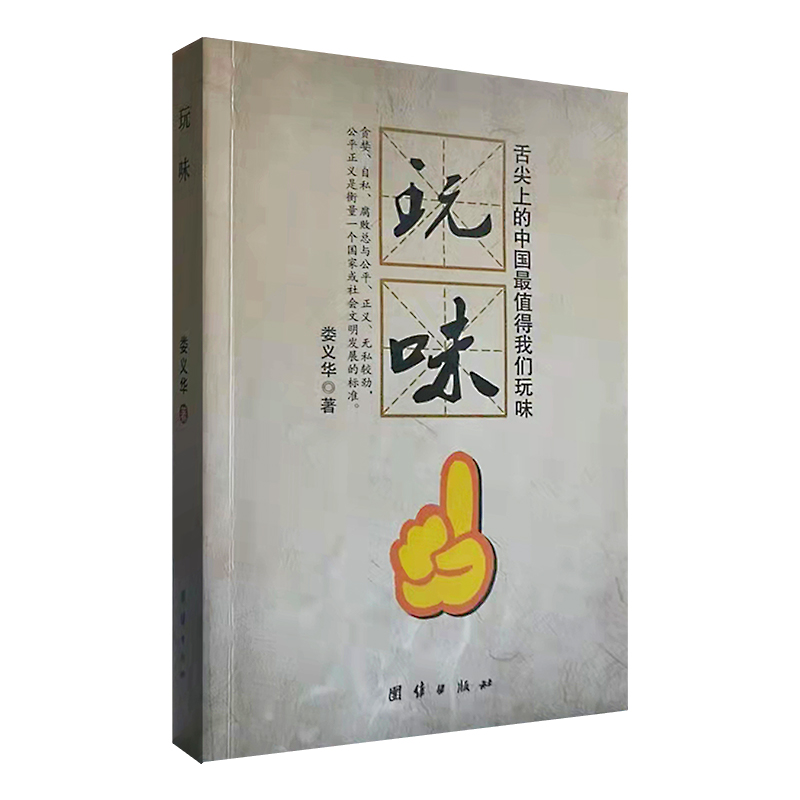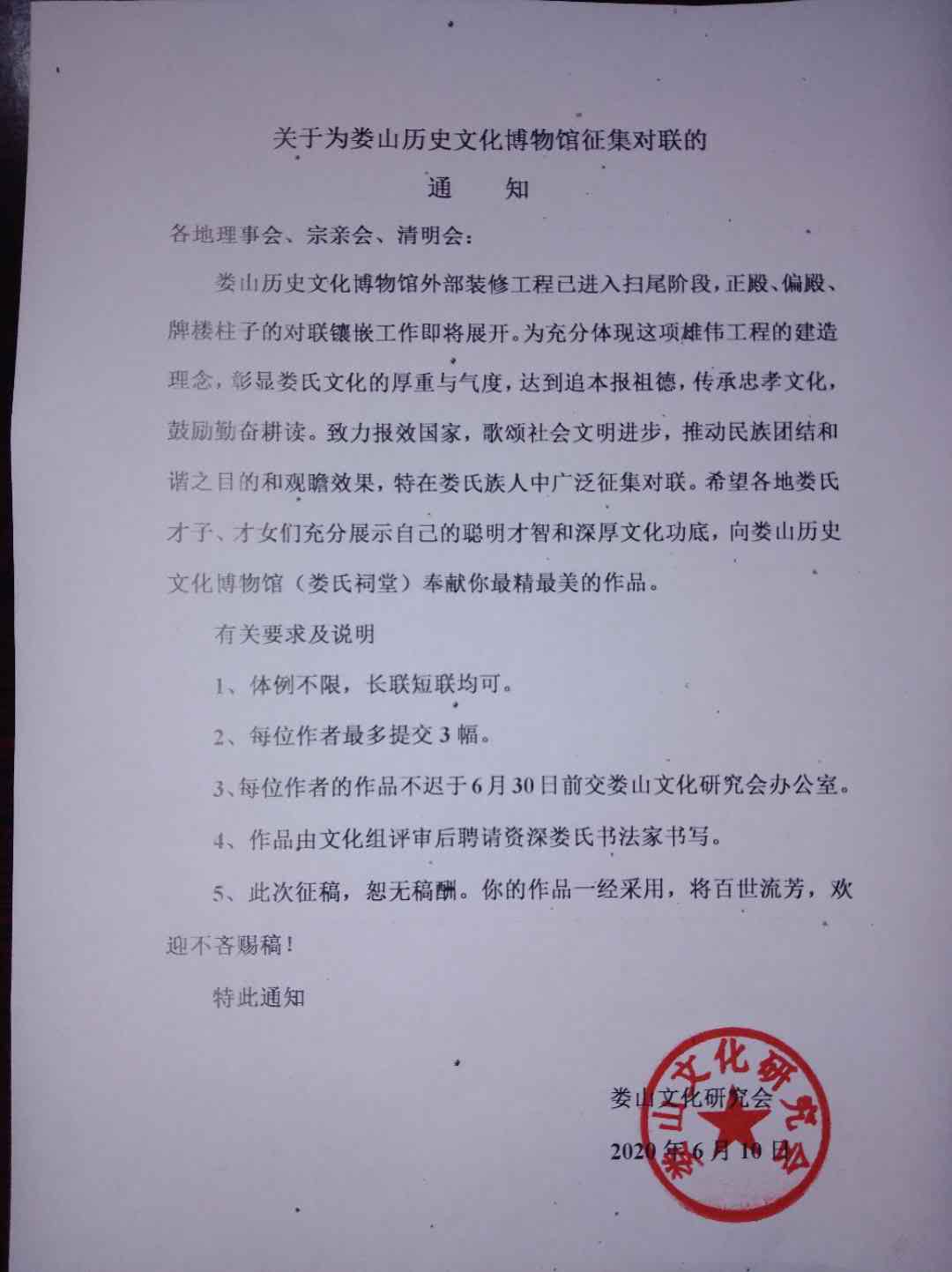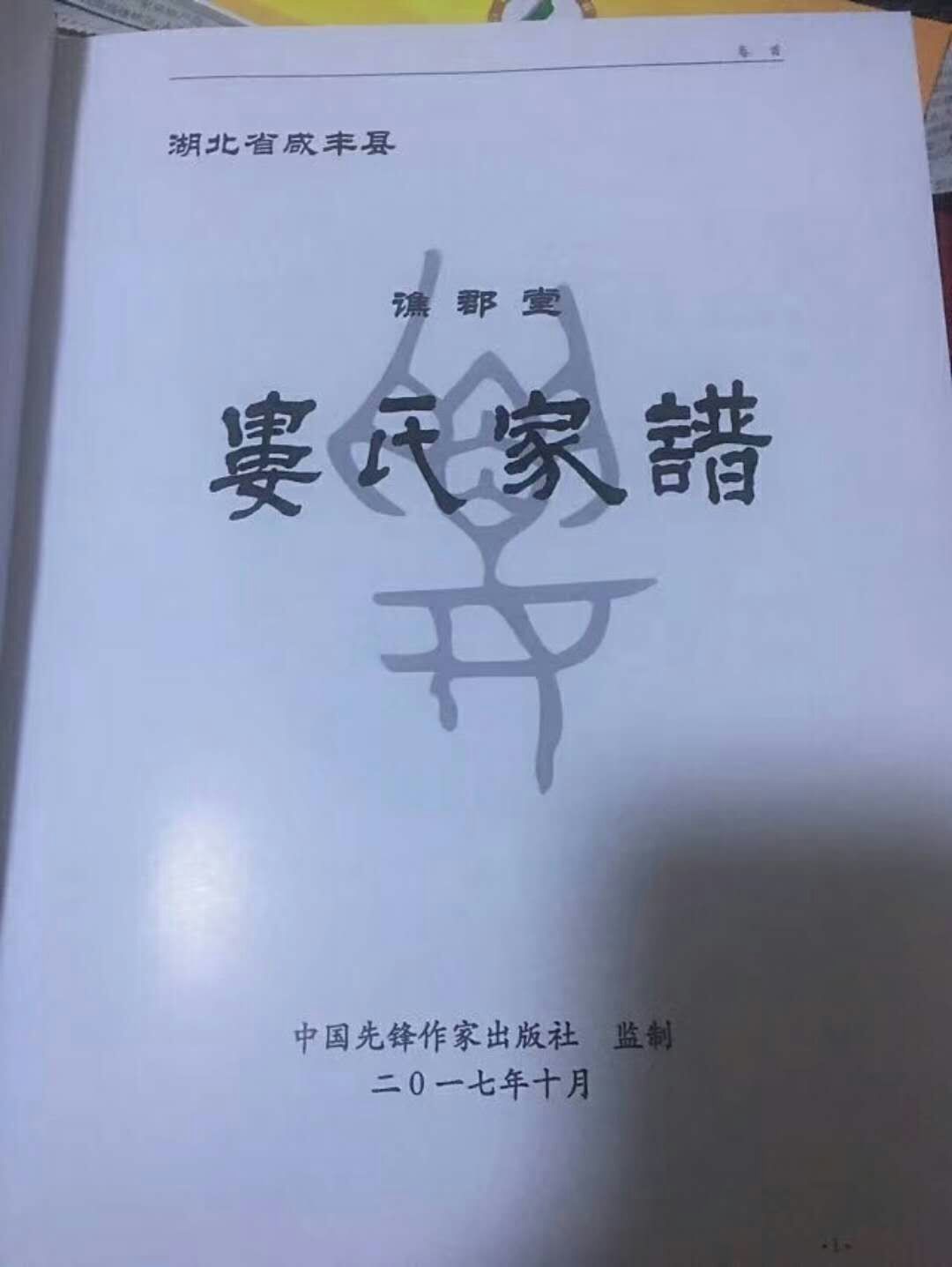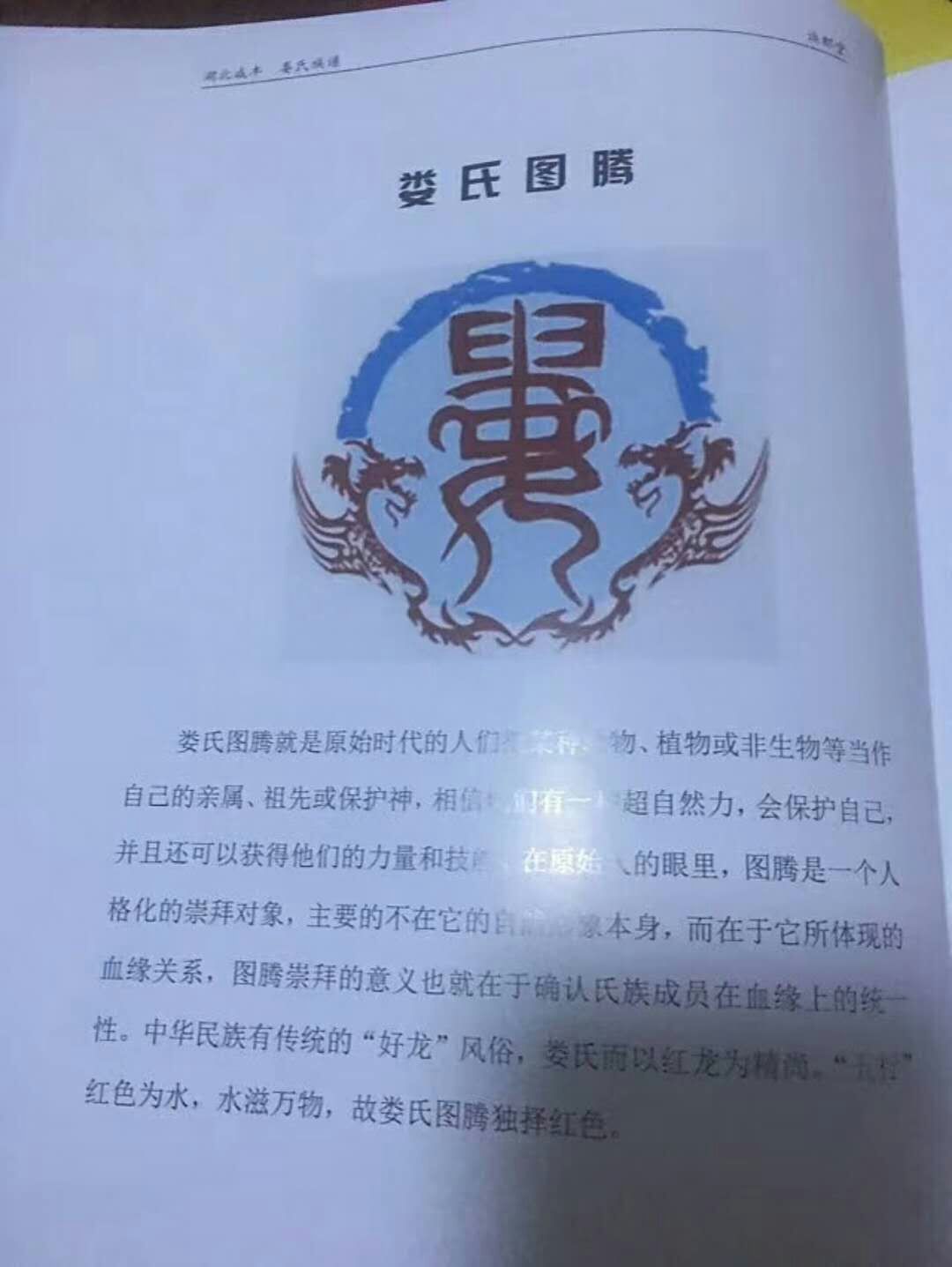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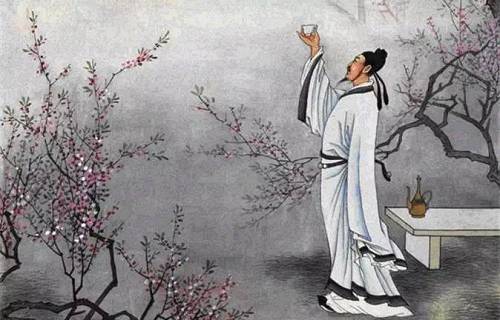
[摘 要]李白“长流夜郎”是文学和史学界长期未决的问题。明末清初,随着“改土归流”不断深入,在遗迹与传说的启迪下,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即传统的李白“长流夜郎半道承恩赦放还”论和李白“长流夜郎谪居三年遇赦放还”论。前者以曾巩为代表,历史悠久,影响范围较大;后者以张澍、黎庶昌为代表,研究时间较短,名人效应差,影响范围小。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贵州文化的发展,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拓展,新的证据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也多样化。使得李白“长流夜郎谪居三年遇赦放还”观点,更合乎历史的原貌。本文作者以考查唐代人对李白的表述为研究起点,还原一个真实的唐代李白。在深入分析了唐代“夜郎”地望此基础上,运用唐代刑律分析李白所获的“长流”刑,按“长流”刑条例讨论李白案。并结合史料记载,对李白“长流夜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进而,在唐代刑律框架上,分析讨论李白流放时间、地点及行程路线,并用充足的史料证明本文的结论。结论认为:李白不但没有“半道承恩放还”,而且沿长江逆水而经黔州(黔中道治所,今彭水)转抵夜郎。“谪居夜郎三年”(即不少于二十四月),“承恩遇赦放还”归籍。并沿原路顺长江东下,在岳州(岳阳)、江夏、汉阳等处徘徊数月,再沿长江而下经浔阳至当涂而卒。作者以此结论,将李白“长流夜郎”期间的诗作,按时序重新排列成表,说明其第次原因及引证来源,使李白“长流夜郎”的过程更近于历史事实。文章的最后,用有力的证据否定了王燕玉教授的“陆路论”。
唐代诗人李太白以从永王璘之罪,流放夜郎一事,史料中记载极为简略。[唐]代正史文献不记,只魏颢《李翰林集序》载有:“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后晋]刘昫等纂《旧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云:“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又[宋]欧阳修,宋祁等纂《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曰:“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至此,虽然表述约有不同,但李白因从永王璘获罪,流放夜郎之事,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与此同时,随着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对李白诗文收集、整理、研究的深入,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云:“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自始,李白流放夜郎事件的起止时间地点,行驶路线,到没到过夜郎等,一直是文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以李白生平记载为背景,唐代刑律为判据,唐夜郎的社会环境为参考系。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证李白长流夜郎历史,对李白有关“夜郎”的诗文,按创作时序从新排序。
一、认识唐代的李白
今天的人是永远不会认识到第一历史的,只能在第二历史上尽可能让历史真实一些。王立群教授说:“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都不一样。”由于史料的缺失,今天人们对李白生平经历了解,更多是基于传播的历史,这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是绝对不够。要认识李白,只能通过李白自述,或与之有交往的人记载中去认识。通识李白自述篇目,《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与韩荆州书》又云:“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赠张相镐》再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及所著诗句“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罗。”和“先君怀圣德,灵庙肃神心。”综其自述,李白自己都不能确定其祖先是李耳、李广还是李蒿?籍贯是陇西、楚江、广汉、还是金陵?因此,在其交往的亲朋好友的著述中错综复杂,即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及社甫诗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这就是李白生世之迷。一个李白自己都不能破解之迷,后人又怎能妄加求取呢?笔者认为:诸如李太白族属、家世、国籍等问题的研究,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唐]代的李白,并非今天人们心中的伟大诗人。从自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按《新唐书·食货》记载:玄宗时期,“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比较之,读者对此怎么看?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 与李白直接接触,并一起生活,留有著述的人不多,魏颢是其中之一。在魏颢笔下李白,除诗赋了得外,并没特别之处。更有些沉浸于酒色的世俗形象。至范正传时,已经是葬身荒野,孤魂难寻,遂迁墓重修。见过李白的晚辈裴敬,在其《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云:“享名甚高,后事何薄。谢公旧井,新墓角落” ……“贵尽皆然,名存则难,故予重名不重官。”可见,晚[唐]时的李白,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大。
李白社会影响力的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的李白,只是集道学、文学、酒色,好交友,勤于笔耕的一般诗人,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力。至北宋,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在李阳冰、魏颢遗著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李白诗稿,并编著内容丰富的宋本《李太白文集》,由此才漫漫有了今天的伟大诗人李白。李白生活的年代距《李太白文集》现世,已经300多年了,《李太白文集》记载内容,已只是对历史生活中李白的一种可能的追述而也,疏理、考证、推测,甚至想象、杜撰、编造,亦成历代学者不同选项。因此研究李白,必须让自己心态回归历史,以唐代的李白为基础,运用合理的疏理、考证、推测,还原其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二、正确理解唐代刑律的“长流”刑
(一)唐代的“长流”刑
李白从永王璘获罪,照例当死刑。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改为“长流夜郎”,已经是重罪从轻,降刑处罚了。按《旧唐书·刑法》记载:“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八:……流二千里者,赎铜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赎铜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赎铜一百斤。 ……又有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谋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十恶者,不得依议请之例。”查《唐律疏议》与《旧唐书·刑法》记载同,均无“长流”刑记载。据《太平广记·卷121》“长孙无忌”条引[唐]张鷟《朝野佥载》载:“长流”由宰臣长孙无忌奏请设立,“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但《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云:“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虽然两说并不相符,但并不能否定“长流”刑的存在。《旧唐书》记载:最先受“长流”刑的人,是右相李义府父子。按《旧唐书·李义府传》记载:龙逆三年(663年),因请术士望气,聚敛钱财。“按皆有实,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
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哀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罚,宜从遐弃,以肃朝伦。可除名长流巂州。其子太子右司议郎津,专恃权门,罕怀忌惮,奸淫是务,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亦宜明罚,屏迹荒裔。可除名长流振州。’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洽、千牛备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皆凭恃受赃,并除名长流延州。”时隔三年,“乾封元年(666年),大赦,长流人不许还,义府忧愤发疾卒,年五十余。”……又时隔八年,“上元元年(674),义府妻子得还洛阳。”由此看出,“长流”刑不但存在,至李义府父子后还是常用之刑。“长流刑”是比“死刑”轻,又比“流刑”重,间于“死”和“流”之间的罪行。依《唐律疏议》可知,唐代是一个刑律非常完善的国家体系,李白“长流夜郎”原本就是从宽处理,没有理由途中恩赦回籍道理,按刑律李白之妻宗氏,也应该随李白一同流配夜郎。据陈玺《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统计,唐代可确定的“长流”案例有六四件,长流百人以上。
自唐高宗起,“长流”已成常态,在“长流刑”者中,死于“长流”期间的约占总人数的44%,多数为先流后诛(赐死);除名、配流家人,永未还籍的约占总人数的20%罪犯,变“长流”为迁徙荒野,任其自生自灭的。赦宥还籍者,有史可稽的不足十人,占“长流”总人数的12%;还有占总数24%的“长流”者,未知其后果。尤其是唐肃宗朝,运用“长流刑”更为平凡,六年就有七人“长流”。其中高力士、孙蓥二人因李辅国陷害获罪;李逢年、第五琦二人因经济获罪;侯令议因失守罪;只有张均和李白同属“从逆反叛”,所不同的只是“内乱”与“外患”而也。在唐代刑律中“从逆反叛”是重罪,涉及两案的其他人,全部获诛,只有张、李两人由“死刑”降“长流刑”免诛。据此分析,李白“长流夜郎”没理由短期赦免,就是“谪居夜郎”三年得赦还籍,已经是奇遇了。
(二)“长流”刑的执行
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四(条)“犯流应配”记载:“三流俱役一年。(本条称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外从户口例)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疏》议曰:妻、妾见已成者,并合从夫。依《令》“犯流断定,不得弃放妻、妾。”(第)二十五(条)“流配人在道”记载:“诸流配人在道会赦,计行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疏》议曰:“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诉(沿诉:指顺水、逆水)程各不同。但车马及步人同行,迟速不等者,并从迟者为限。又《大唐六典·卷3》记载:“……水行之程,舟之重者。诉,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诉,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百里,余水七十里。”并且还对长江三峡、风雨等特殊情况,作了补充说明:“其三峡砥制[制当作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当填以案]记,听以年功。”由此可知,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李白获“长流夜郎”罪,已经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妻子宗氏按律得配流夜郎。又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五(条),及《大唐六典》之规定:李白长流夜郎的行程是有日期限制。以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古代部分》记载为参考,[唐]肃宗时期,已经是“万斛大船风行成都、扬州之间”景象;从“涪州东至江陵府,水路一千七百里”里程。木船在长江上日程, “重庆—宜昌段一千三百里,下水约十天,日行一百三十里左右;上水约三十五天,日行三十五里左右。”因此,李白从获刑上路到流放地夜郎,徒行时间不会超过七十天,并且是在吏卒的押解下带枷锁而行。并非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沿路与朋友观湖游寺,喝酒迎诗作赋,形似游山玩水的朝廷重犯。
三、唐代李白长流地夜郎
李白对夜郎表述,最早是[唐]天宝八年(749年),为其好友王昌龄自江宁丞贬为龙标慰,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据此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李白长流的夜郎,龙标西,夜郎在东,才有“夜郎西”的说法,从而产生了夜郎湖南沅陵说,事实上并非如此。
古西南有夜郎国、夜郎郡、夜郎县记载甚多,见于本文研究的是李白长流夜郎,故将时限确定为唐代。研究唐代夜郎,有《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就成书先后而言,《元和郡县图志》最早,成书于[唐]宪宗年间,距李白生活年代只数十年,只惜此书图卷散失;次为《旧唐书·地理志》晚于二百多年;《新唐书·地理志》更晚至三百多年。通识三书,两唐书记载“夜郎”内容约同,均为三处,即夷州“夜郎”、奖州“夜郎”和珍州“夜郎”,唯《旧唐书》较《新唐书》更详而也。但《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夜郎”内容只有两处,即珍州“夜郎”和奖州“夜郎”。为此本文就以《元和郡县图志》和《旧唐书》中“夜郎”议论之。
[唐]代地方行政管理以“道州县”三级制,以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为时限,之前分全国为十道,之后分全国为十五道。其中之一是分江南西道增置黔中道,而[唐]代所有“夜郎”县郡设置,始终在黔中道管辖内,并县是有严格时段意义。虽然在不同地点设置“夜郎”,但并没有同时出现两个“夜郎”设置。按《元和郡县图志·卷第30》记载:“江南道黔州观察使,……管州十五:黔州、涪州、夷州、思州、费州、南州、珍州、溱州、播州、辰州、锦州、叙州、溪州、施州、奖州。县五十二。”与新旧唐书比较,完全相同的有十二州;同地异名有二(即《旧唐书》奖州曰“业州”;叙州曰“巫州”),新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均记载了名称演变过程,并变更时顺相同,如《元和郡县图志》奖州条下云:“本[汉]武阳县地,贞观八年(634年)于此置夜郎,属巫州。长安四年(704年)于此置舞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鹤州,二十年(732年)又改为业州,大历五年(770年)又改为奖州。……管县三:峨山、渭溪、梓姜”;《元和郡县图志》叙州条下云:“贞观八年(634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天授二年(691年)改曰沅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沅’‘原’声近,复为巫州。天宝元年(743年)改为潭阳郡。大历五年(770年),以境接叙浦,改为叙州。……管县三:龙标、朗溪、潭阳”;记载相异的有二(《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无“涪州”;《新唐书》无“珍州”),其原因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以有确切解释。《元和郡县图志》涪州下云:“武德元年(618年)立为涪州,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故为名。上元二年(761年),因黄莩硖有獠贼结聚,江陵节度吕諲请隶于江陵,置兵镇守。元和三年(808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曰:‘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输纳往返不踰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余里,途经三峡,风波没溺,颇极艰危。自隶江陵近四十年,众知非便,疆理之制,远近未均,望依旧属黔府’”。又《新唐书》溱州溱溪郡条云:“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山洞置。……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县五:荣懿、扶欢、夜郎、丽皋和乐源。其中“夜郎,(中下)贞观十六年开山置珍州,并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后为夜郎郡,元和三年(808年)州废,县皆来属。”据此,李白长流时,黔中道辖十四州及一郡,即黔州、夷州、思州、费州、南州、溱州、播州、辰州、锦州、溪州、施州、业州、涪州、珍州、潭阳郡。
按《旧唐书》记载:最早在夷州置夜郎县,即“武德四年(622年),置夷州于思州宁夷县,领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宣慈、慈岳等十三县。……贞观元年(626年),废夷州,省夜郎、神泉、丰乐三县,……。”据此,夷州夜郎县设置只有四年,即(622—626)年;第二次在业州(即巫州或舞州、鹤州、奖州)设置夜郎县,即“贞观八年(634年),置夜郎县,属巫州。……开元二十年(733年),改夜郎为峨山县。”据此,业州夜郎县设置有九十九年,即(634—733)年;第三次在珍州(溱州)设置夜郎郡县,即“珍州(下),贞观十六年(642年)置。天宝元年(743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珍州。领县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夜郎、丽皋、乐源。由于夷州夜郎县存在时间短,《元和郡县图志》中并无记载;而业州和珍州两州,存在长达九十一年同名异地的两个夜郎县,即(642—733)年。因此史学上曾产生了两夜郎县的混乱记载,是容易理解的。按《元和郡县图志》珍州条下记载“夜郎县(中下)郭下、丽皋县(中下)郭下。右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与州同置,三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随所畲种田处移转,不常厥所。”表明:开元二十年(733年)前,夜郎为县名,并且以业州夜郎为主,珍州夜郎小变化无常;开元二十年(733年)后,珍州夜郎曾一度改为郡或县,并且夜郎一名一直保留至唐朝结束。
综上所述,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载:“随风直到夜郎西”中的夜郎指业州夜郎县,在龙标(当时为潭阳)附近,李白作诗时,夜郎、龙标均为天宝元年前的县名。李白长流夜郎是在“安史之乱”后,此时夷州、业州夜郎早已经成过去式了,黔中道只有珍州夜郎存在,所以李白长流夜郎只能是珍州夜郎,即今遵义桐梓夜郎坝。
作者简介:游云学,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物理学教学与教育文化研究。
原载《娄山魂》2018年第一期
阅读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