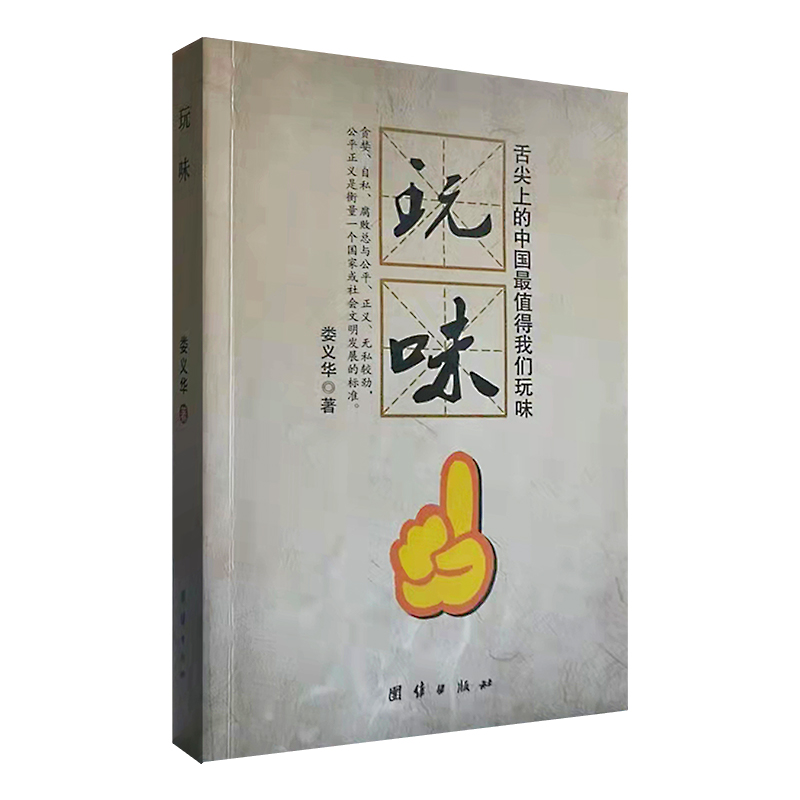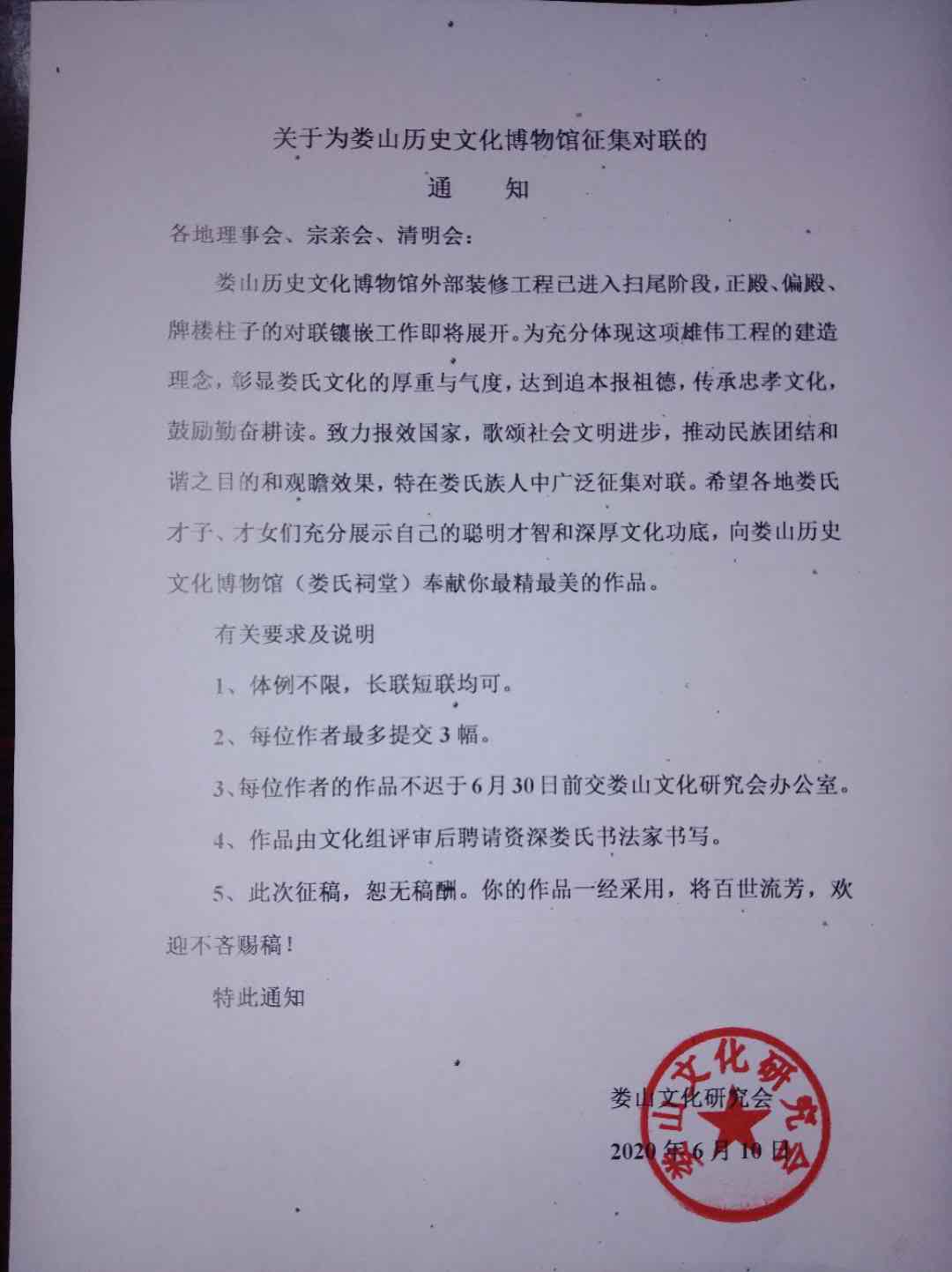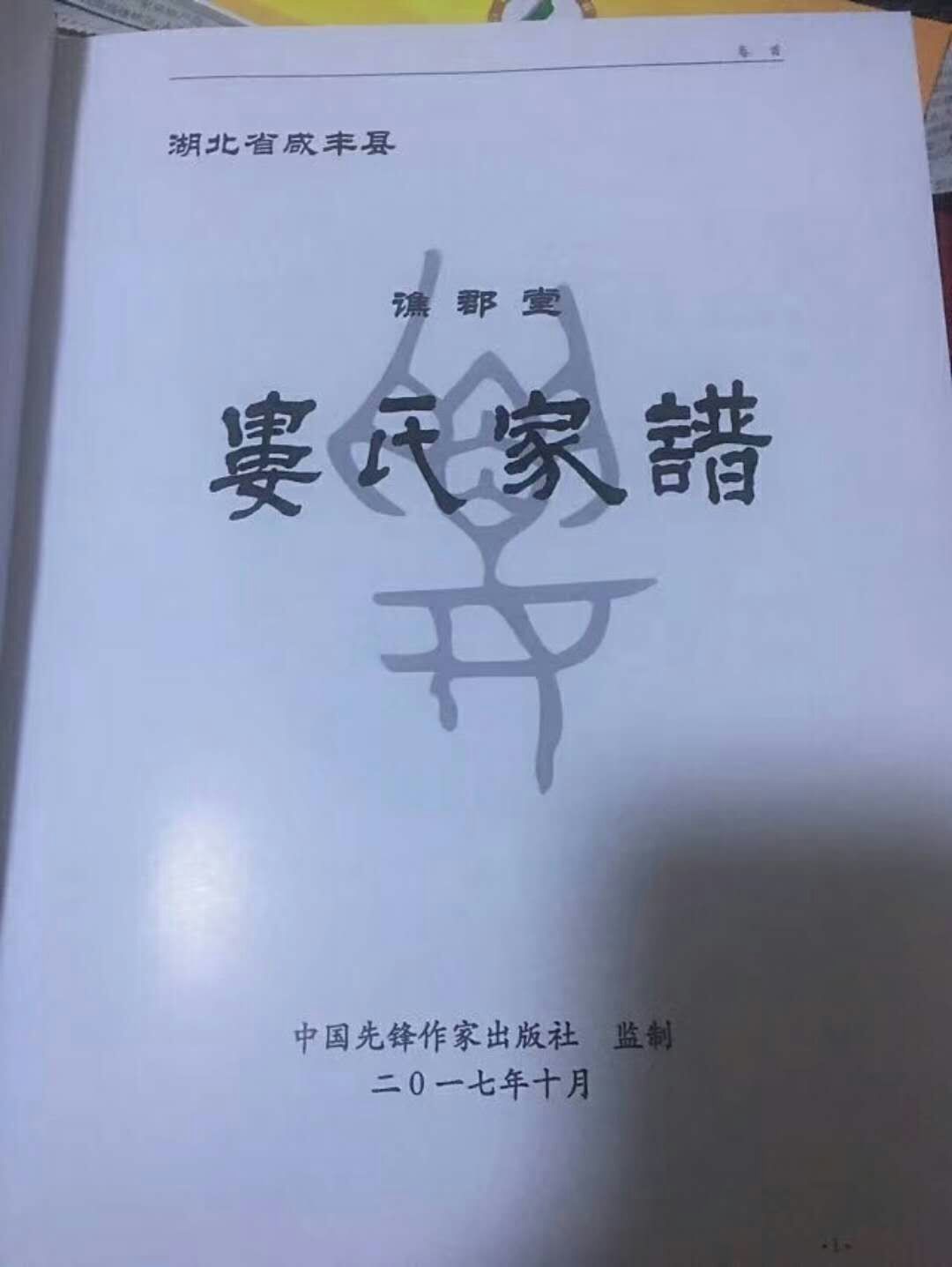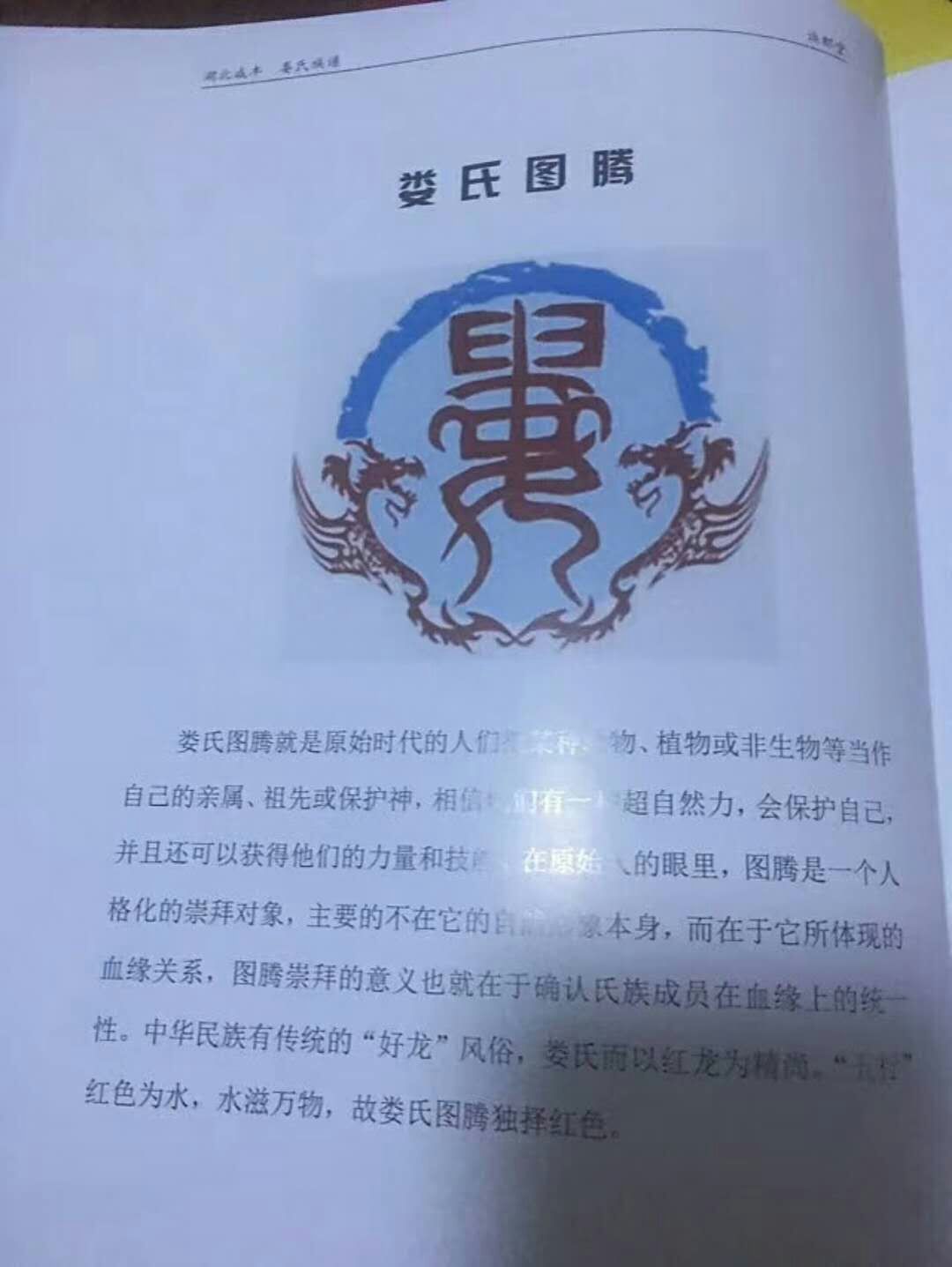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下)
(接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

五、李白关于“夜郎”诗作时序考证
李白诗作时序研究,是文学、史学界永恒的课题,早在北宋,曾巩就全面研究了李白诗作时序问题,为李白文学创作经历勾勒了完整的初型。历代李白文学研究者,均十分重视李白诗作时间的研究,只有弄清作者创作诗作的时间、地点及背景,才能正解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学者黎庶昌是系统研究李白有关“夜郎”诗作时序第一人,他在《李白至夜郎考》中以用李白诗作时序,论证了李白“长流夜郎”行程路线,及“谪居夜郎”的结论。由于对李白“长流夜郎”缺乏唐代刑律分析,也没有考查《册府元龟》相关记载,没得出李白“谪居夜郎”确切时间。因此,对李白关于“夜郎”诗作时序只有一个大致认识,并且还存在不足之处。
李白关于“夜郎”的诗有三类:一类是诗的标题直书“夜郎”,即有明确指向,是因“长流夜郎”而撰作品,这样的诗有十二首;另一类是诗内有“夜郎”、“迁客”、“南迁”等二字,表明部分内容与“夜郎”有关,这样的诗有九首(其中不计标题和内容均含“夜郎”);再一类是虽然没有明确写有“夜郎”二字,但其诗表述的内容与“夜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诗作。这类诗作,历代学者对其定界差异很大,按黎庶昌《李白至夜郎考》及相关研究表明,这样的诗有十四首,共计三十五首。其中,除《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和《秋下荆门》作于[唐]开宝和天宝年间外,其余三十三首全部作于李白“长流夜郎”后的晚年,即(757—762)年的五年间。作者晚年如此关注“夜郎”,亦间接证明其“谪居夜郎”的事实。通过对李白“长流夜郎”行程路线(流放和归还),及“谪居夜郎”时间的讨论,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李白“长流夜郎”期间的诗作进行重新排序,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由此按时间路线将李白这一时期诗作排序总结如表三。
表三:李白夜郎诗创作时序表
序 时间 诗作标题 引证理由及背景说明 时段
之前作品 开元间 秋下荆门 黎庶昌误认为“流夜郎”时作,但因时令不符,李白恩赦归还在春夏,不应该在秋季,故疑似开元十三年作。 流放到夜郎前
天宝间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诗中“夜郎”并不是他流放的夜郎,是指业州夜郎县(今湖南与贵州两省相邻处),邻近龙标。
1 至德二年
(757年)
十一月后 流夜郎赠
辛判官 流放时与朋友的赠别诗,诗中有:“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诗意表明,作者即将流放夜郎,但还没有起程,对夜郎充满了未知感。
2 至德二年
(757年)
十一月后 赠刘都使 流放时与朋友的赠别诗,诗中有:“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诗意为:我感谢明主(皇帝)不杀(指由死刑降为流刑)之恩,心怀哀痛地接受长流夜郎的现实。
3 至德二年
(757年)
十一月后 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西塞(今黄石),是浔阳沿长江而上的一水驿站,诗中有:“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 说明作者是逆水而上,且去的道路艰难漫长,心情忧郁。
4 至德二年
(757年)
十二月后 上三峡 诗中有:“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表明帆船逆长江而行的艰难。李白一生逆长江而上只有这一次,即流放夜郎。 流放到夜郎前
5 至德二年
(757年)
十二月后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目壁 诗中有三个地名,即巴东、瞿塘峡和巫山。历代学者均将巫山理解为巫山县,但李白理解的巫山不是巫山县,是巫山山脉,由此李白登的是山脉中的那一座最高峰并不确定,按作者另首诗《宿巫山下》可证,李白的巫山指白帝城。因此诗题应该理解为:自巴东经瞿塘峡至白帝城(登巫山最高峰)。
6 至德三年
(758年)
二月前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 这是一首争论较大的诗,诗中有两个地名,即夜郎和乌江。其争论点是对乌江的定位,主流学者认为乌江指浔阳九江支流,但亦有学者认为指今贵州乌江。又诗云:“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白帝晓猿断,黄牛过客迟。”更表明妻宗氏及妻弟宗璟随李白而行,并且过了黄牛峡及白帝城,到了贵州乌江才分别,是否“乌江”是早就有的俗称,只是不载入史册吧。这从唐代刑律角度理解,也是十分合理,在刑律上夫妻间有株连关系,即流配制度。
7 至德三年
(758年)
二月前 流夜郎闻
西酺不预 本诗标题“闻西酺”是一特殊信息,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中均记载:肃宗朝七年,只有至德二年十二月,大赦天下,“赐酺五日”;其它期间大赦天下,均无此记载。
8 乾元元年
(758年)
乾元二年
(759年) 巫山枕障 诗中有:“巫山枕障画高丘,白帝城边树色秋。”黎庶昌认为李白是在秋季“长流夜郎”,所以认为此诗作于流放途中的巫山。但从全诗写意来理解,此诗更象是对经过巫山的回忆。 谪居
夜郎
9 流夜郎
题葵叶 葵叶,古代葵菜,又名冬苋菜。鲍照有《园葵赋》。李时珍云:“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种之者颇鲜”。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因为古代特种单调,疑为李白“谪居夜郎”时的主要蔬菜,只是后来种者亦“颇鲜”了。李白借此特殊植物,抒发自已流居远乡情怀。
10 望木瓜山 木瓜山,黎庶昌《李白至夜郎考》中有专论。“木瓜山有三,一在介休;一在清阳木瓜铺;一在常德府城东七里。”…“考[唐]之夜郎县在今桐梓县夜郎里,而夜郎里有木瓜庙者,当为白贬至之所。”至今桐梓县还存有木瓜山、庙、镇等名。
11 题楼山石笋 本诗出于碑刻,通过道光《遵义府志》才入学者视野。原本未载入[清]代前
乾元元年
(758年)
乾元二年
(759年 题楼山石笋 的《李白诗集》,近代出版的《李白诗集》收入其中。疑点:楼山,即娄山。学者均知唐代并没有此山记载,按《遵义府志》记载,娄山原名不狼山或黑神垭。又据《娄梁族谱》记载,因其人名“娄珊”而改名,这已是唐末之事,远晚于李白时代。这似乎与“乌江”一样的困惑,是否“娄山”、“乌江”均为早就有的俗称,只是不载入史册吧。按诗的出处及诗的内容而论,确指今天的桐梓娄山景象。 谪居
夜郎
12 南流夜
郎寄内 诗题及内容指向均明确,是作者久居夜郎,想念自己妻子诗:“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此诗亦为李白谪居夜郎的直接证据之一。
13 乾元二年
(759年)
三月后 放后遇
恩不沾 李白所犯之罪,不论后世学者认为判得公正与否。在唐代就是死刑,当诛。能从死刑减降为长流刑,已经是奇迹了。无论是死刑还是长流,按唐刑律都要株连妻儿父兄。同时从“长流”刑减为“流”刑也应该有过。《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等典籍中,查不到一个由死刑或长流刑直接恩赦放还的例证。所以李白理应有由“长流刑”减降为“流刑”,再由“流刑”恩赦放还的过程。
14 赠别郑判官 诗中有“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二年是明确的时长,并没有得到赦免放归。其中郑判官疑似黔中道的一官员,李白谪居夜郎二年后,遇此官书赠的一首诗,表明作者盼望归籍心情。
15 乾元三年(760年)二月后 流夜郎半
道承恩放
还…… 因为诗题云“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历代学者均以此为据,证明李白长流夜郎未遂,半道巫山遇赦放还。仿佛没有什么好议论,李白是没到夜郎,半道就承恩回江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太多理由否定这里的“半道”说法了,对此请读者见表后专题分析。
16 留别龚处士 黎庶昌认为此诗是流放前的留别诗,但从诗的内容看,更象是离开夜郎归籍前所作的赠别诗。李白谪居郎夜最少已有近三年,虽然当时夜郎没有什么文化名人,但如龚氏这样的处士应该有。如果认为龚处士是居住于夜郎的朋友,李白遇赦放还时作诗留别,其诗的内容就恰如其分。正如诗云:“龚子栖闲地,都无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我去黄牛峡,遥愁白帝猿。赠君卷葹草,心断竟何言。”
17 上元元年(760年)二月后 早发白帝城 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学界均认为该诗作于李白流放遇赦免后,归籍经长江顺流而下途中。诗的内容反应了作者惊喜交加,归心似箭心情。亦形象地刻画出乘舟东下快感,借以抒发作者的爽快心情。 承恩归还
18 江行寄远 从诗的内容可以体会到,作者乘舟顺长江东下,已经进入长江中下流情景,因江上的船已经要借助帆的力量行驶了,但仍日暮千里的速度而行。
19 江上赠
窦长史 诗中有“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指明曾流放于夜郎,并在那里谪居三年。由此,诗中的夜郎,是作者的追述和回忆。
20 留别贾舍人至二首 贾至,唐官员诗人。按《资治通鉴》记载,至德二年(757年)六月,因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县令,当死免诛。中书舍人贾至上表议刑律法令,群臣皆劝皇上接受贾至建议“守贞观之法。”但肃宗并没认同。又有《全唐文》为肃宗制《册回纥为英武威远可汗文》为据,贬岳州应在乾元元年(758年),直至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复为中书舍人散骑常侍。因为贾至(758—762)四年间,均在岳州为官。但按贾至的做人原则(《资治通鉴》记载甚详),精通唐代刑律的贾至,绝对不会和身犯重罪的李白作如此亲密交往。所以,李白、贾至、李晔、裴隐四人游洞庭,只可能发生在李白遇赦回岳州时。
21 上元元年(760年)五月后 张相公出镇荆州…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 张相公,即张镐。李白因从永王璘获叛逆罪下狱浔阳,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左右,李白在浔阳狱中,由“死刑”减降为“长流刑”,张镐帮助过李白,有诗《赠张相镐•二首》为证。按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张镐于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因反对肃宗接受史思明请降,被“罢为荆州防御使”。……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再次反唐。肃宗思张镐反对史思明请降的进言,征拜张镐为太子宾客,改左散骑常侍……。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岐王李珍作乱,“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镐尝买珍宅故也。”诗中已经有“除太子詹事”,由此可知,该诗理应在李白长流夜郎后,承恩放还至江夏时,得知张镐的事而作。
22 上元元年(760年)五月后 经乱离后天
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本诗为李白自传体长诗。按本文分析,李白长流夜郎,流放时罪犯,没有自由权,从浔阳至夜郎有时限,不可能在江夏久留。按诗的内容:“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忽弃贾生才。”均表明该诗作于长流夜郎后,李白在承恩赦归还籍时,途经江夏,在江夏会友唱和了数月,继续顺江东进。 承恩归还
23 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 按本文分析,李白钦定为“长流”罪犯,地方官绅避之不及,还敢设宴于“兴德寺南阁”?这在唐代官制中,是于情不合的事,就是在今也有高调行事之疑。其诗的内容:“天乐流香阁,莲舟飏晚风。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并没有罪人的忧郁之情。如果将该诗理解为李白承恩放归时,经留江夏会友,朋友为其赦宥放还的接风洗尘,更合乎其作诗背景。
24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云:“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表明作诗时间是赦放后。过去的一段时间,作者生活在夜郎,长时间没有动过笔。从全诗内容看作者极度自由,表现出人老心不老舒畅情怀。
25 江夏赠韦
南陵冰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云:“君为张掖近酒泉,我窜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表明作诗时间是赦放后。
26 江夏使君
叔席上赠
史郎中 “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李白遇赦归来,在江夏又邂逅老友,自是惊喜交并,恍若梦寐。李白在江夏与朋友饮酒作乐,盘桓了数月,继续顺江东进。
27 与史郎中
钦听黄鹤
楼上吹笛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表明作诗时间是在赦放后。诗的一二句写谪居夜郎时的回忆,期盼回家而不得回家的心情;三四句写现实,本是五月江城,通过笛声《落梅花》,将听者带入了冬天。
28 上元元年(760年)八月后 泛沔州城
南郎官湖
•并序 与上首诗同期作,本诗有序,是李白诗作中极少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一首。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 但这一记载与李白长流夜郎时序矛盾,如果认为是流放夜郎时,李白在汉阳所作,李白从浔阳逆水至汉阳用时近一年(九个月),这怎么可能呢?又李白作为钦定“长流”罪犯,汉阳官绅为什么如此接待一名钦犯呢?他们就不怕因此而株连自己吗?细读诗全文:“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诗中李白及朋友们“逸兴”、“秋月好”、“为欢古来无”,这与“长流夜郎”罪犯极不相配,并且在饮酒作乐中,应朋友邀请,将“南湖”更名为“郎官湖”,这太不合时宜,再超脱的人,也不可能达止境界。反之,李白承恩赦还至汉阳,朋友们为李白获释放聚会一起,诗酒朋侪,兴致赋诗作序,更合乎史实。因此序中所记载的“乾元岁”有误,应该是“上元元年”。
29 醉题王
汉阳厅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中王汉阳,就是前首诗序中的汉阳宰。又诗云“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诗中自喻鹧鸪鸟,经长流夜郎遭遇后,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只求与朋友饮酒作乐,取醉而归。
30 赠王汉阳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题赠王汉阳,是离别王汉阳时赠诗。诗云:“天落白玉棺,王乔辞叶县。一去未千年,汉阳复相见。……”表明王汉阳与李白是故交,在叶县曾经有过一次分别,今天又在汉阳相见。……。
31 寄王汉阳 与上首诗同期作,诗题寄王汉阳,表明是离开汉阳后作。诗云“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账郎官醉,罗衣舞女娇。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别后空愁我,相思一水遥。”充分说明,李白从夜郎回到汉阳时,朋友们热情接待李白,饮酒作乐,歌舞升平的情境,别后作者十分留念那段生活。
32 流夜郎永
华寺寄浔
阳群官 李白承恩归籍,在江夏、汉阳等处与朋友们郊游唱合一段时间后,顺水东进回浔阳,浔阳官绅朋友为李白接风洗尘。所以诗云:“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又
32 上元元年(760年)八月 流夜郎永
华寺寄浔
阳群官 从全诗内容而论,这次聚会李白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这样多官员朋友欢迎自己,所以在永华寺喝醉了。另一方面浔阳是他伤心的地方,在这里入狱流放;按李白后来留居当涂推测,当时妻子宗氏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有“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的悲伤。 承恩归还
33 忆秋浦挑
花旧游时
窜夜郎 李白承恩归籍,在浔阳短暂停留后,继续沿长江东下,至秋浦(今池州市),在此作了此诗。诗云:“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
通过表三,明确地将李白“长流夜朗”划分为三段,即“流放”、“谪居”、“归籍”。有“流放”、“归籍”用时短,诗作多,“谪居”时间长,诗作少特点,有李白诗自证:“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又有“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又据李白诗:“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和“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比较,认定李白的巫山泛指巫山山脉,实为白帝城周边的某山,从而形成顺长江而下:巫山(白帝城)—瞿塘峡—巴东,及逆长江而上:巴东—瞿塘峡—巫山(白帝城)地里次序。又有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逆江而行的情境,李白逆长江而上的流放路线,是其它任何理由都无法撼动的史实。

六、余论
除源自曾巩的李白 “长流夜郎半道巫山承恩放还”的推论外,还有王燕玉关于李白“从江夏向西南行,过洞庭溯沅水经武陵、辰(以上今湖南)、锦州、思州、费州、夷州、播州进入珍州达夜郎县(以上今贵州)”的陆路推论,尚须说明之。只因对黎庶昌引证李白诗没有“夜郎”而起,王燕玉教授为此另辟一说。该论说的主要依据:李白、贾至、李晔、裴隐四人游洞庭湖诗作。但细考诗文,除一首《留别贾舍人至二首》有“君为长沙客,我独之夜郎。”从诗句意亦能读出,贾至迁岳州与李白流夜郎为同时,并已经是过去的事。反而证明:此时不是流放而是归籍时。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理由否定王燕玉教授的推论,①王教授本人也对陆路推论认为“证据虽不多,却比较有力。”但体会不出什么证据有力。王教授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贾至《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对此分析如下:从地理上看,岳州(今岳阳)水道枢纽,由此可沿长江而上入川,沿洞庭南下沅江入黔,也可入岭南。李白、贾至、李晔、裴隐在岳州相遇,贾至和裴隐在岳州为官是主人,李白、李晔均为过客,《全唐文•贾至》载:《册回纥为英武威远可汗文》有“维至德二年岁次丁酉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即乾元元年前,贾至还在肃宗皇帝身边,又有贾至《送于兵曹往江夏序》云:“予谪居洞庭,岁三秋矣。”,即(758—762)年的四年间,在岳州就有三年;又据《旧唐书•李岘传》记载:乾元二年(759年),“凤翔七马坊押官,先颇为盗,劫掠平人,州县不能制,天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擒获决杀之。其妻进状诉夫冤。辅国先为飞龙使,党其人,为之上诉,诏监察御史孙蓥推之。蓥初直其事。其妻又诉,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讯之,三司与蓥同。”也就是说:贾至、李晔、李白、裴隐的相遇只能发生在乾元二年以后。由此可知,李白“长流夜郎”的同时,贾至也贬为岳州司马,李白在夜郎、贾至在岳州各自谪居了三年(虚年),李白承恩放还后相遇于洞庭,时间应该是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②正如本文“李白夜郎诗创作时序表”中所论述的那样,贾至、李晔均为精通唐代刑律之官,即使再好的朋友关系,也不可和一名“长流”钦定重犯,在洞庭湖上如此畅游,这有“欺君之罪”之嫌。③李白、贾至、李晔、裴隐四人游洞庭湖诗,按诗文内容均表明在秋季,而李白流放是在冬春两季,遇恩放还是在春夏时两季,难与“长流夜郎”相遇联系。④无论是曾巩的“长流夜郎半道巫山承恩放还说”,还是王教授的“陆路论”。均存在李白流放途中,行程时间长达近一年的特征。如此自由的李白,还是一个钦定“长流刑”的重犯吗?⑤按王教授的“陆路论”有力证据《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李白应该由洞庭经长沙、衡阳至零陵,与“从江夏向西南行,过洞庭溯沅水经武陵、辰(以上今湖南)、锦州、思州、费州、夷州、播州进入珍州达夜郎县(以上今贵州)”陆路论差别很大。在唐代,陆路由今天的湖南入贵州至桐梓,均要经过大唐与南诏两国的势力区,通行难度很大。⑥李白“长流夜郎”的第一目的地并非夜郎,而是成立未久的黔中道所在地黔州(今彭水),再由黔州转至夜郎,因为必须有一个押解官吏交接和移籍过程。因此,水陆两路优劣显而异见。诸多证据和推理均否定“陆路论”。
贾至的诗除《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外,还有《送李侍郎赴常州》、《送李侍御》、《长沙别李六侍御》及《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及《别裴九弟》等。有“侍郎”或“侍御”之差,有向东赴常州者,又有别于长沙者,又有南下零陵者,十分杂乱,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从略之。
(作者:游云学 ,原载娄山文化研究会《娄山魂》杂志2019年第二期)
阅读 次